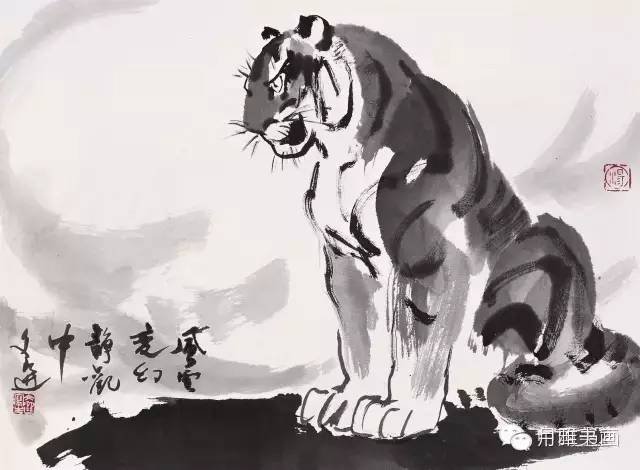![1]() 你忘了孙悟空喜欢楷书!
你忘了孙悟空喜欢楷书!
一
孙悟空喜欢楷书?
这不是我胡说八道。
话说孙悟空方从石头变猴的那会儿,天天跟着各种红黑屁股的畜生闲游烂逛,一日泡澡泡到一处山涧,突然发现远处是一股瀑布飞泉。
那帮畜生此刻也爱好起祖国大好河山,不禁发出感慨:“好水、好水”。
这时,一个二货突然说,哪个有本事钻得进去,他就是我爹。
这时,石猴孙悟空跳出来,说,你妹,老子敢去!
现在,只见石猴孙悟空两眼一闭,蹲下身子,将身一纵,嗖一声,就跳了进去。
跳进去这个地方,就是水帘洞。
你看好,孙悟空跳进去后,看到一个桥,走到桥中间,在正当中一块石碑,是圆头的,上面写着“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什么字体?看清楚哦,《西游记》里写的是一行“楷书大字”。
经此一跳,孙悟空成为了花果山的大王,水帘洞成了孙悟空的御用宫殿,而且时至今日,没有任何文献记载显示,孙悟空当上大王之后,将“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这一行“楷书大字”铲平换成其他字体。
自己的家,自己政府的办公大楼门前的风水石碑,使用的是楷书,你能说孙悟空会讨厌楷书吗?
二
当然,现在说孙悟空喜欢楷书,还为时尚早,但我们一定知道孙悟空不喜欢什么书体。
孙悟空不喜欢什么书体?权威解读告诉你:篆书。
虽然你可能不情愿,但这是真的。
纵观孙悟空历经的九九八十一难里,凡是妖怪、坏蛋或者丑八怪在的地方,门头牌匾、对联和各种有书法的装饰,书上总会提示有篆字体的存在!!!
比如,猪八戒加入取经创业团队后,在行过八百黄风岭,西进一脉平阳之地时,突然遇到一条狂澜大水,但四望却没有船通。
唐僧这下慌了,开始兜着马叨逼叨了,这时,他偶然发现河岸上有一通石碑,上面有三个“篆字”——流沙河。
正是因为这个篆书的提示,接下来,师徒三人发现水里——“滑辣的钻出一个妖精,十分凶丑”。
又如,第一次乘老乌龟过的河什么河记得吗?通天河!通天河什么字体?书上特别写“篆文大字”。
![2]()
![]() 再如,孙悟空找丑八怪牛魔王借芭蕉扇,而牛魔王跑老龙精处喝酒,龙精安排了三四个蛟精服侍,当时,孙悟空见到的陈设,是廊庑上挂着些虾须的帘子,屏障上写着“鸟篆之文”。
再如,孙悟空找丑八怪牛魔王借芭蕉扇,而牛魔王跑老龙精处喝酒,龙精安排了三四个蛟精服侍,当时,孙悟空见到的陈设,是廊庑上挂着些虾须的帘子,屏障上写着“鸟篆之文”。
还如,孙悟空变成桃子,让想和唐僧做夫妻的妖精吃下去那一集,妖精宅邸,匾上用字,乃“鸟篆”是也。
三
接着告诉你,唐僧师徒三人在遇到流沙河的时候,见到的那通石碑上,除了篆字写着“流沙河”而外,实际上还有一首诗,曰:
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
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
这首诗是说,流沙河很深很急很翻滚,鹅毛和芦花那么轻飘的东西直接翻到水底。言下之意,可怜的人猴猪,你们颤抖吧。
好,这首诗是用什么字体写者?书上特特别别讲——“(碑)腹上有小小的四行真字”。
真字,就是楷书,只此一句,结合水帘洞楷书大字,《西游记》作者对字体的审美和价值观就明明確確!!
一方面,《西游记》里,有篆字的地方必有“反派”,从无例外!篆字是反派符号;
另一方面,流沙河是收沙僧的地方,沙僧会成为唐僧创业团队一员,所以,在篆字碑上再补上一段楷书,喻示此地妖怪亦邪亦正。
不仅如此,你要特别注意,为什么这首诗是“小小”地写在“碑腹”,而不是碑阴,或者像“通天河”那样,写在碑角,而且连什么字体都没有说?
好,这正是写作练家子的地方。简单一通碑文的字体以及位置和大小,道尽流沙河之妖,乃是一内在(碑腹)善而表象恶(篆书大字)的家伙。
名著这样读。
四
为什么《西游记》会把有为数不多的楷书字体委派给主角?
这很好解释。“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是也!
那为什么《西游记》又把所有的篆字派给妖怪坏蛋和丑八怪呢?
这并不是篆字不好或者什么的,答案还是因为这字体人不易认识,叫人古怪而已。
可以肯定,《西游记》里没有特别点名的各种地名和牌匾,如雷音寺、敕建宝林寺等,亦皆是楷书,为何?易于别人认的生活常态而已。
启功先生十分鄙视武则天《升仙太子碑》,因为这碑用草书入碑,而草书一般人不易认,立个碑,本来是让人看,因为自己设置一道装逼屏障,最后是别人很少看懂,很少深究,结局只剩下了自娱自乐,传播效率大打折扣。
武则天升仙太子碑
我国文化讲究照顾别人,不陷入自我利益的无限争夺,所谓“仁者爱人”,所以最后恰恰是“爱人者,人恒爱之”——你觉得启功深受爱戴,是因为书法真牛到顶天吗?
不,启功先生的书法极其简单,因为简单,所以难,他是个认真写字的人,一笔一划写字的人,为别人望得懂看得清,甚至积极写简体字,要知道,抨击简体字抵制写简体字的书法家,是大有人在,而且那个圈里可谓六畜兴旺。
启功和武则天的这个故事,只能说,人的境界和格调,很多时候是很容易被人一眼洞穿的,洞穿的那个标的物,有时候,就仅仅是流沙河那块碑。
而结合《西游记》里的字体观,现实里也说得通,只有古怪的人,才会写不易别人认的字,写字小道,最见心性,此话绝非虚言。
五
其实,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孙悟空为什么就喜欢楷书了?
首先,唐僧师徒,最后取到的《涅槃经》《菩萨经》《虚空藏经》《首楞严经》等等经,书上说,上面写的是楷书。
没有理由相信经过九九八十一难取到真经,孙悟空内心是厌恶不欢喜的,爱屋及乌,猴之常情,孙悟空因为欢喜取到的经而喜欢楷书,是必须的。
其次,孙悟空的师父,是叫做唐僧。
唐僧(600—664),男,俗姓陈,小名江流儿,法号玄奘,号三藏,被唐太宗赐姓为唐。为唐朝著名和尚。
我们知道,唐代最牛的书法,是楷书。目前,敦煌出土的唐人《涅槃经》《菩萨经》《虚空藏经》等等唐僧取回的经典抄写本,只有楷书,且煊赫至极。
![3]()
![]() 敦煌唐人写经
敦煌唐人写经
孙悟空拜在唐僧门下,从小耳闻目濡,对楷书情有独钟,是一定的。
更重要的是,据书法一瞬斋最新获得的一份唐代资料显示,孙悟空本人,也是唐代一位杰出的楷书大家,由于这份材料过于破烂,待修补整理完毕,就分享给大家,望能耐心等待。
同时,为庆祝伟大的取经家孙悟空本命年,书法一瞬斋联合尹飞卿童鞋,在丙申年为我国人民推出抄经和写敦煌抄经体小楷之服务。
因为尹飞卿有日书万字的书写量,从《心经》到《金刚经》《涅槃经》《菩萨经》《虚空藏经》等等一切佛经,无论字数再多,尹飞卿均乐于接件。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