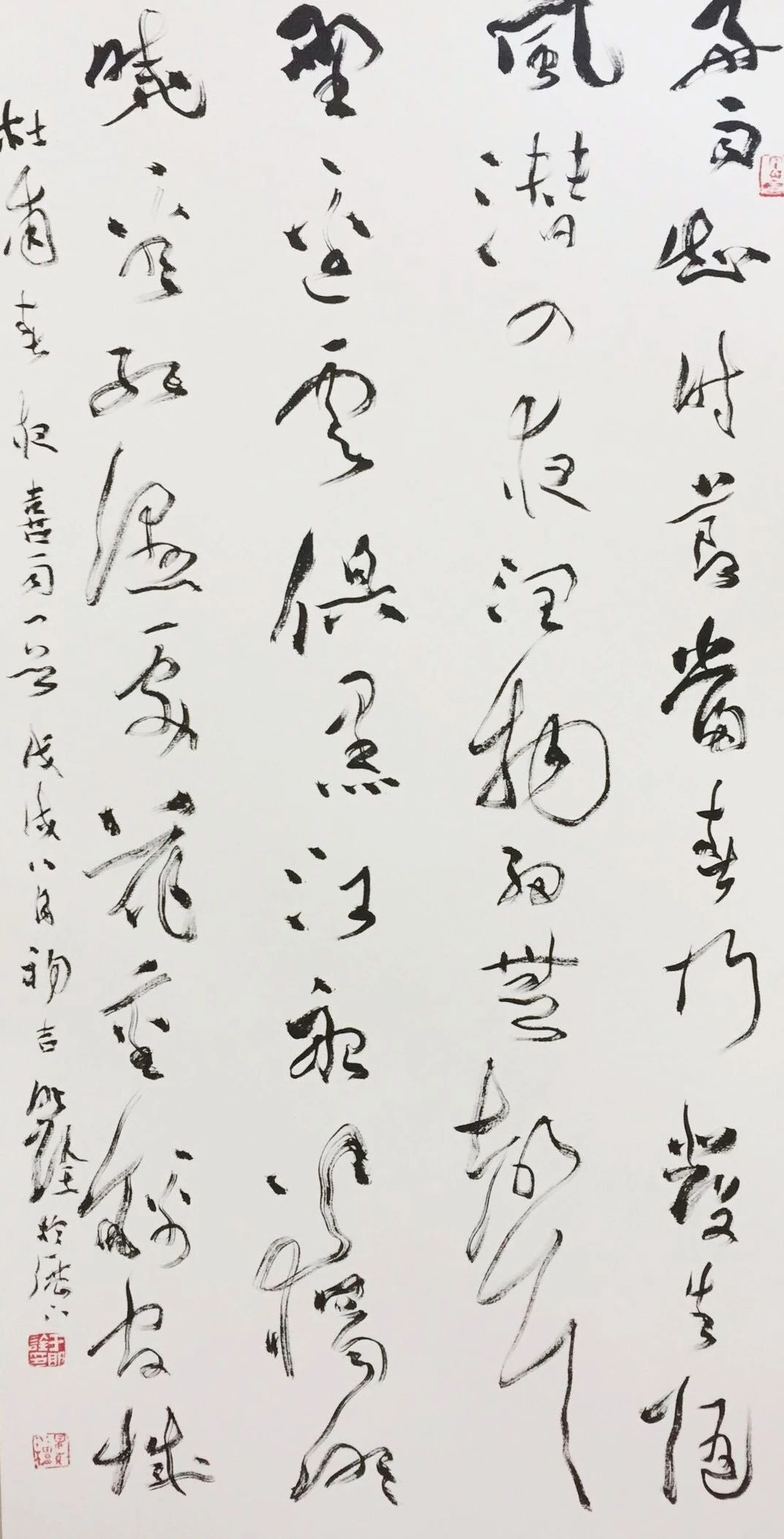书法教育不是知识教育而是艺术教育,因此说,书法教育≠知识传授+技法训练。也就是说,不把书法教育简单地分解为两个部分,即知识传授(包括书法史,古代书论,美学常识,历史知识等)和毛笔技法训练(等同于写毛笔字)。这种理解显然是只重表面形式,而忽略了书法教育作为一种艺术教育的本质。
十几年来,我国的书法教育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就高等院校书法教育现状看,许多艺术院校和部分师范院校都开设了书法艺术专业,招收专科、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许多普通高校也都开设了书法课。
然而,各类院校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效果都存在着很大差异。除中央美院和中国美院外,多数师范院校的书法教育均存在忽视对学生“创作意识”的引导与培养问题,仅注重知识传授与基本技法训练。至于多数普通院校开设的书法课,虽冠以“艺术”之名,其实不过如旧式教育中的“临帖、描红”教学一样,只是教学生写“大仿”,写“毛笔字”而已。
我们知道任何艺术都是表达作者的主观感情和个性的,书法艺术当然也会一样。这正是书法艺术作为一门艺术而存在的内质所在。反映在书法教育上,我们的目的当然要力求通过有关知识的传授和相应的技法训练使培养对象更好理解书法艺本质,更好地运用书法艺术形式以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艺术个性。前者是手段,而后者才是目的。手段再重要,我们也不能仅仅为手段而手段。
否则,知识掌握得再多,也难免不是纸上谈兵;技法再熟练,也仅仅是“写字匠”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种观点误认为,美院是培养艺术家的,自然应该重视学生创作水平的培养与提高;而师范院校培养的对象是书法教师,当然就要注重有关书法知识学习和基本技法的常规训练而应淡化学生的创作意识。
其实,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很难想像,一个自身创作能力较差只会照本宣科的写字匠会成为一名合格的书法教师。即使是一书理家如果在艺术实践方面蹩脚,也注定只能是空头的理论家。
正如诗人所言“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躬行”就是亲自实践,在这里,就是唤起培养对象的“创作意识”,注重创作实践,在创作过程中体味和印证书学理论,从而使培养对象在自觉的创作状态与过程中体味书法艺术的本质与真谛。
在这问题上,前人曾有反复论述如,邕认:“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项穆《书法雅言》也说:“书之为言,散也,舒也,意也,如也。
欲书先散怀抱,至于如意如愿,斯可称神。”古人反复强调的“散也,舒也,意也,如也。”无非就是指艺术创作的状态,换句话说,就是要使学书者自觉地进入角色。不进入角色,找不到艺术创作状态,终不能理解书法的神妙。
试想,历史上的每一件书法经典作品,不都是作者在这种特定的创作状态中去完成的吗?如果没有这些作品及其创作,那些书法大师还存在吗?如果他们都不复存在,那么书法艺术又将是什么,在哪里呢?
总之,书教育尤是高等校的书教育,应该充分重视其艺术教育的特性,应该把创作意识的培养和创作实践的指导放在应有的重要位置上,而不能仅仅重视书法相关理论知识的传授和一般的技法训练。
我们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鉴于当前部分高校尤其是有一些师范院校的书法教育系科在实施教学的过程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如下的几种偏见。
其一,重知识而轻实践
古人主张“先器识而后文艺。”大意是说一个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修养。这里的“先”与“后”只是表明知识文化修养对于从事艺术创造的重要性,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前”与“后”的关系。就书法学习来说,知识的积累和文化修养对于一位书法家或书法工作者来说,自然是非常重要的,这一功课应该是终生的。
然而,掌握知识、加强修养的目的是什么呢?最终是要体现、物化到我们的作品中去,要用我们的创作去体现。同时,这些知识、修养也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准确更直接地掌握艺术创作的规律。古人主张“由技入道,技道双进”正是这个意。
如果“技”不能过关,何谈“入道”?“道”又在哪里?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种片面认识,误认为创作是水到渠成的事,只要先了解了书法理论知识,慢慢地写总会把字写好的,创作水平的提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的事。
且不说书法史是古代代表性书法家、经典碑帖及风格流派的知识介绍,书法美学是借助于美学研究的工具,分析说明书法作为艺术的美的原因,古代书论仅是书法家创作的心得体会,就是各种书体的技法研究等课程也是如解剖麻雀一样的“实验室手段”。
常识告诉我们,一只麻雀可以解剖分割为羽毛、鸟骨、血肉等等,但这些东西凑在一起就是一只活的麻雀吗?然不是。清代书法理论家笪重光说:“精美出挥毫,巧在于布白”如果不自挥毫操练,不具体地经营筹划章法布白,那书法艺术的“精美”与“巧妙”如何去体验与把握呢?
其二,重临摹而轻创作
在书法学习过程中,临帖与创作是相辅相成的、互补互动的关系。临帖是规整和修正自己,是被动地去适应古人创的规范,亦即我为宾古人为主;而创作则相反,要我为而古人为宾把对古代碑的领悟与理化为自家的创造,展示出来。
亦即古人所说的“散也、舒也、意也、如也”,可见两者并不矛盾,非但不相矛盾,惟有两者同时进行,效果才能更佳。因此,在对学生进行具体的临帖创作指导时,要强调临创并重,不可偏废。
王铎主张“一日临帖,一日请索”是很有道理的。目前,在不少高等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只有到毕业时才会拿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创作,平时几年除了学习理论课就是规规矩矩地临帖。这显然是误解了两者的关系。适当增加创作辅导时间,强调临创结合、临创并重是非常有益的。
我国美术教育自五、六十年代起,就提出“临摹—速写—创作”三位一体的教学原则实践证明是正的、成功的,对目前尚不成和完善的书法教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其三,重古人而轻今人
书法艺术是传统艺术,自甲骨文时代始,至晋唐、至明清,以至近代、现代、当代,其发展源远流长,其间风格衍变,流派更迭,极其丰富。我们尊古人,学习传统,但也不能厚古薄今,一味尚古崇古,认为越古越好。
有观点认为,晋唐以上为“源”而宋明清到民国均是“流”。此论或许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我们如果根本不入“流”,又如何“上溯源头”呢?“源”启发哺育了“流”,而“流”都是“源”的自然延续,更是“源”的丰富与发展。倘若没有“流”,“源”也会成为“一潭死水”。
同时,书法历史告诉我们,历代书风流派的更替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历代大家与他的前任相比,都有各自不逊前人的新创造,即如近现代于右任、林散之等一代大师,也同样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建树了毫不逊于古人的又一丰碑。
因此,从书法史的角度看,厚古而薄今是没有什么道理的。至于认为一切以“二王”为正宗,“二王”之外无书法个别观点更是片和狭隘了。还有者,认为当代书报刊不可看,当代书法展览不可看,把当代书法的某些风格特点视为歪门邪道洪水猛兽,就更属浅薄了。
事实上,每个书家都是不可能完全不受其时代书风影响的,黄山谷学苏东坡、颜真卿学张旭、王献之学王羲之而王羲之学钟繇更属人人皆知的常识了。关键是在学习中不为名家风格所囿,如林散之先生称赞王献之那样—“跳出龙门是真龙”。
其四,重共性而轻个性
当代书法教育尤其是高等院校书法教育,改变了传统的师徒相授的旧方式。显然,这种改变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它所具有的规范性、科学性、逻辑性、合理性和系统性是旧式书法教育所不可比拟的。
然而,由于其玄秘顿悟式的旧式教学手段被科学理智的分析论辩所代替,也由于书法审美教育中先入为主的强化刺激,还有与受教育者群体之间的相互熏染与感化,必然使受教育者形成审美趋同心理。
其结果是:
(一)消解创作的激情和冲动;
(二)受教育者自身潜能的消失;
(三)在创作上趋于雷同。(参见徐利明《论书法高等教育中的审美趋同心理》,载《全国第四届书学讨论会论文集》)
总之,突出了共性而消除了个性,这是现代书法教育中应该引起我们充分注意的一个负面问题。
试想,我们的教材千篇一律,讲到每位书家、每件碑帖,几乎都是面面俱到的“套词儿”,如《兰亭序》如何体现“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的魏晋风度,《祭侄稿》又如何体现家仇国恨的撕心裂肺,让我们的学生怎样在欣赏去寻找那些属于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呢?
如果经过几年专业学习,一个调子说话,一个模样写字,只是提倡合乎“传统”的共性,而消解他们独特的审美个性,他们的创作意识则必然弱化,其创作能力也就必然消退。那样的结果,就会不可避免地使书法教育的培养对象变成传声筒式的空头理论家和以描摹各家各派为能事的写字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