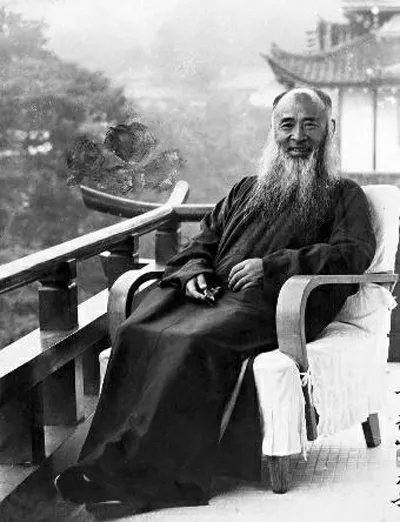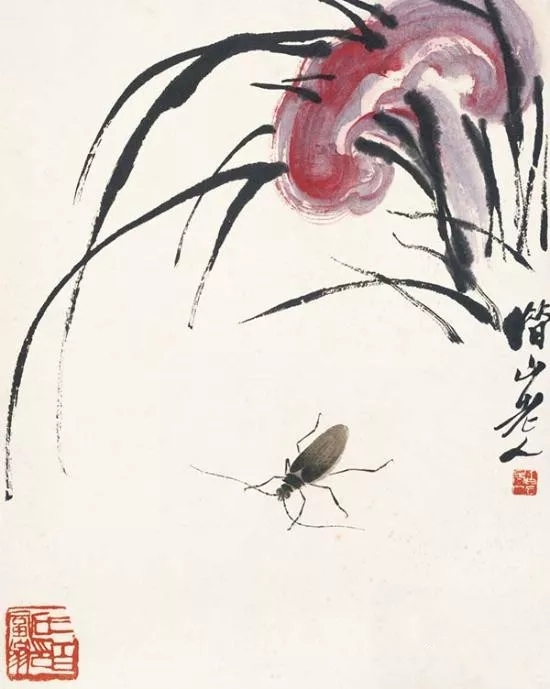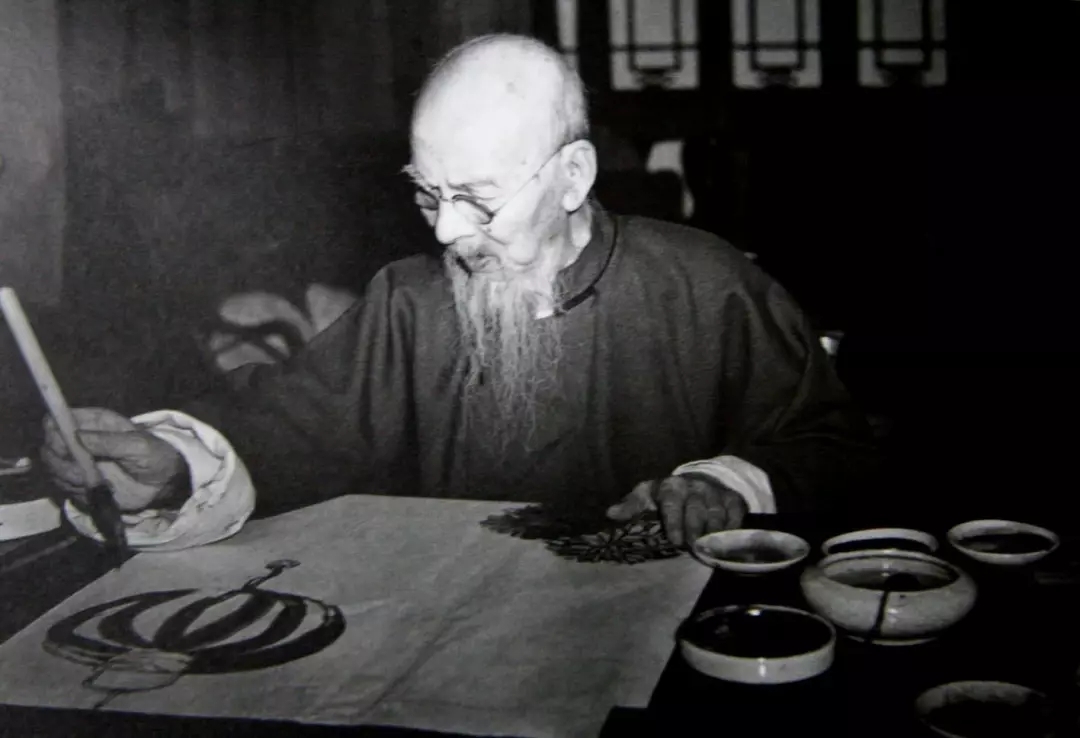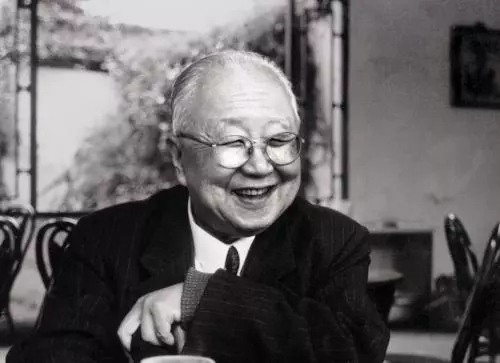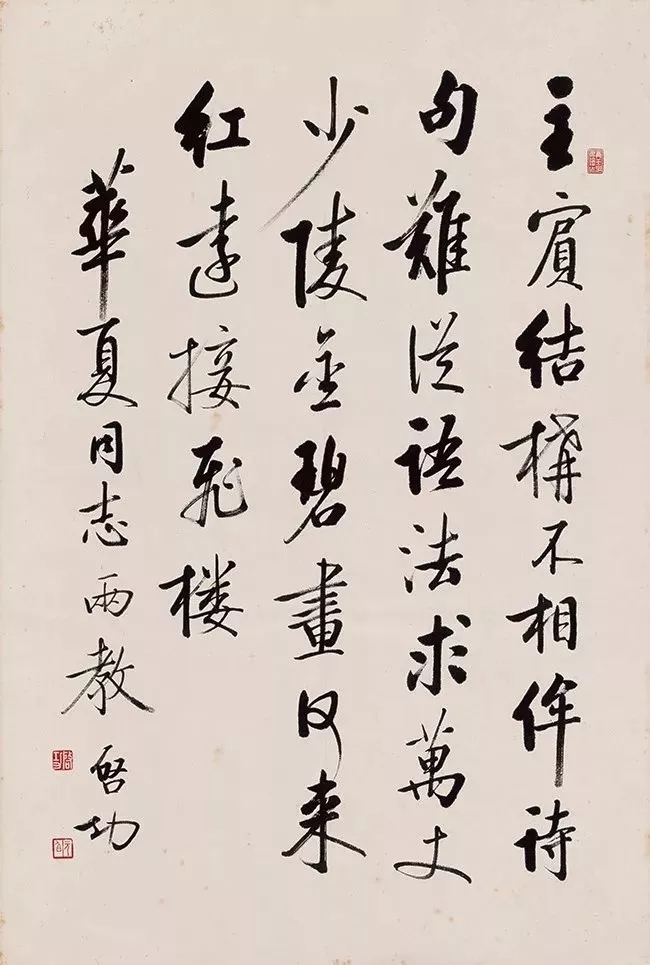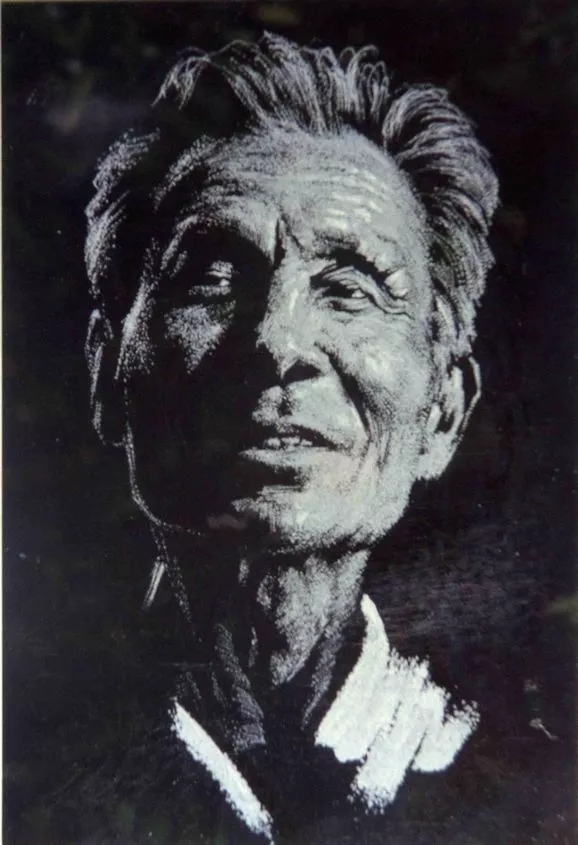冯小刚的电影《芳华》,又在媒体圈里刷了一回热点。
有人看到战争,有人看到乱政。
我看到的,却是至今难得的,无雕琢的美。
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全国最美丽的女孩子,在部队文工团。
没有漂亮衣服,没有脂粉。
只有日复一日的舞蹈练习,枯燥中的纯粹。
清一色的绿军装,清瘦骨架也能撑起来的年轻气盛。
玩水是仅有的几件乐事之一。
如日光洗练的少年少女,乌黑的发和健壮的身体。
这些,
都是放在现在,也绝无仅有的,绝代风华。
我们在怀念什么呢?
那时候人们风骨纯粹,一心只有一两件事所寄。
我们总说那时的人们好看,那时的人们风雅。
我们怀念以前的文人墨客,怀念旗袍和匠人手艺。
我们想念的那些。
对于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呢?
我想说一些,值得我们怀念的事。
张大千先生,手下一笔漂亮的荷花。
长年一席长袍和一缕美须,身上仙风道骨得来他早年遁入佛门的经历,那时他被赐号大千。
那样一个本该与世隔绝的人,却是一个爱玩的画家。
他爱吃如命,擅长做美食,画了很多萝卜白菜。
在这幅画着萝卜白菜的作品里,张大千写了一首石涛的七绝:
“冷淡生涯本业儒,家贫休厌食无鱼。菜根切莫多油煮,留点清灯教子书。”
在萝卜白菜里,能看出对着残烛读书的性质,此种人间烟火的诗意,在今日,谁还会记得?
齐白石的虫子,比其他任何画精细,是众所皆知的。
有一次,他看娄师白画螳螂。
问他:“你数过螳螂翅上的细筋有多少根?仔细看过螳螂臂上的大刺吗?”
“螳螂捕食全靠两臂上的刺来钳住小虫,但是你这大刺画的不是地方,它不但不能捕虫,相反还会刺伤自己的小臂。”
这般固执的精细,源自童年时的山村生活。
那时生活苦闷,父母无暇顾及,齐白石还被称为阿芝,他只能漫山遍野地寻找虫子玩。
他观察蛐蛐打架,观察蚂蚱的触角。
不论他成为多大的名家,他心里住着的,还是那个漫山遍野和虫子逗乐的小男孩。
他知道,一虫一世界,这才是永远的活色生香所在。
启功是国学大家,但生活中却像个爱开玩笑的老头。
他收藏布娃娃,喜欢和小孩子打交道,人们几乎看不出功名在他身上发生的变化。
他一朋友黄苗子,上年纪后吃多了油腻,脚患痛风住院期间,因为只有素食可吃,因此向启功诉苦。
启功抓着机会,和诗戏答曰:“口里淡出鸟,皆因患痛风。寻常太饕餮,半月不轻松。摄为心如死,医疗地对空。明朝一出院,狂赛马拉松。”
黄苗子出院后,启功又作诗云:“口里淡出鸟,昂然万劫身。飞来天外句,划出世间文。眼比冰川冷,心逾炭火春。娲皇造才气,可妒不平均。”
短短几句诗里,皆是典故神话,就这样稀松平常地做成了打油诗,这种接地气的趣味,实是他内心的一种广阔。
再来说说吴冠中。
谁都知道这个衣衫破旧的老人,是个大画家。
一日,他朋友笑说:“有消息称,你的一幅画又拍了4000多万元,创下新的纪录……”
吴冠中笑笑:“与我无关。”
卖煎饼的妇女和剃头师傅都和他熟络,问他生活里的愿望,他说:“想吃煎饼,但咬不动了。”
他坐在路边摩挲印章,卖煎饼的妇女走过去问他:“你这是做什么?”
他说:“把我的名字磨掉。”
“这么好的东西你磨它……”
他说:“不画了,用不着了,谁也别想拿去乱盖。”
多么贵重的物件啊!为防范赝品,吴冠中破釜沉舟。
但这样形貌单薄的他,却曾写过:
我本不想学丹青,一心想学鲁迅,这是我一生的心愿。固然,形象能够表现内涵,但文字表现得更生动,以文字抒难抒之情,是艺术的灵魂。愈到晚年,我愈感到技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是数千年千姿百态的坎坷生命,是令子孙后代肃然起敬的民族壮景,所以,我敢狂妄地说:‘一百个齐白石抵不过一个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骨会软很多,少一个画家则不然。
原来他们的火焰,都是在内心深处燃烧的。
粗布简食,实是把功夫都放到了对万物的至情中去。
美食里有世界,虫子里有世界,文字里有世界。
我们看《芳华》,觉得那些素颜姑娘和军人小伙惊艳,也许正是粗布简食将他们身上的气质剥离干净。
让我们又再次,看到了人们专注于一两件事时,身上所绽放的风雅和光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