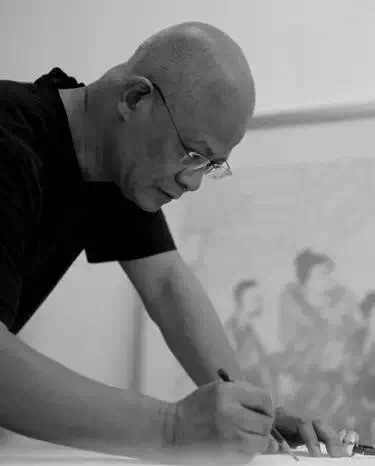怀素禅师接受过全面的笔法教育,对绞转、提按都有较强的驾驭能力;他可以利用他对各种笔法的把握能力,在笔法的丰富性方面同他的前辈进行一番较量……但是,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自叙帖》中虽然偶尔可见到被简化的绞转,绝大部分线条却是出自一种简单的笔法——中锋不加提按的运行。这就是通常认为《自叙帖》出之于篆书笔法的由来。怀素禅师牺牲了笔法运动形式的丰富性,换取了前所末有的速度和线条结构不可端倪的变化。
《自叙帖》中字体结构完全打破了传统的准则,有的字对草书习用的写法又进行了简化,因此几乎不可辨识,但作者毫不介意;他关心的似乎不是单字,而仅仅是这组疾速、动荡的线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线条摆脱了习惯的一切束缚,使它成为表达作品意境的得心应手的工具。线条结构无穷无尽的变化,成为表现作者审美理想的主要手段。它开创了书法艺术中崭新的局面。
速度是作者的另一主要手段。但是《自叙帖》中速度变化的层次较少,因此线条结构变化比质感的变化更为引人注目。笔法的相对地位下降,章法的相对地位却由此而上升。
形式是统一的整体,似乎不应区分各种形式因素地位的高下,但是,书法之所以能成为一门艺术,首先是由于毛笔书写的线条具有表达感觉与情绪的无限可能,因此自从书法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以来,控制线条质感的笔法始终处于最重要的地位;楷书的形成促使笔法简化,使它丧失了人们长期以来习惯的、它曾经具有的丰富表现能力,于是人们不得不转向其它方面,设法弥补遣种损失。这裹虽然仅以草书为例,但是,却具有普遍的意义。自唐代楷书艺术走向全面繁荣以后,出现不少关于字体结构的理论,便绝不是一种偶然现象。
笔法控制线条质感的作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因此,它对于书法艺术从不曾失去应有的意义,但是由于另一形式因素一章法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笔法不得不让出它第一小提琴的位置。
唐代以后,人们强调笔法的呼声不绝,但是无损于这一事实。
赵孟頫是元代鼓吹笔法的中坚人物。他在《兰亭序跋》中写道:“学书在玩古人法帖,悉知其用笔之意,乃为有益。”然而从赵孟頫大多数作品来看,仅仅做到圆润、秀洁而已,用笔颇为单调,运动形式局限于提按,运笔节奏也缺乏变化。
冯班《钝吟书要》云:“赵子昂用笔绝劲,然避难从易,变古为今,用笔既不古,时用章草法便拙。”
“不古”并不能成为艺术批评的准则,但是这段话实际上潜含赵孟頫用笔平淡、单调的指责。“避难从易”,正说明赵孟頫不过是笔法简化趋势中的随波逐流者,而不是涛峰浪谷中的弄潮儿。他既不能像黄庭坚一样自出机抒,又不能像米芾一样溶铸传统。我们并不认为“超入魏晋”是对一位书法家的最高褒奖,但称赵孟頫“超入魏晋”,不过是迷人的神话。赵孟頫对线条结构倒是颇费心力。尽管人们批评他“上下直如贯珠而势不相承,左右齐如飞雁而意不相愿”,但不得不承认他结字熟练而准确,字形虽然基本取之于古典作品,但确实表现了一种秀逸、典雅之美。后人喜爱他的书法,也大多是在这一点上坠入情网的。
明代董其昌也十分强调笔法的作用,但人们对他的笔法却提出激烈的批评,认为他的线条过于“软弱”。仔细观察董其昌的作品,线条果断,但是不够丰实;人们所说的“软弱”,可能主要还是针对“单簿”而言。“笔画中须直,不得轻易偏软”,他是基本上能够做到的,但是运用提按容易出现的单调与单薄之感,他各却终无法摒除。
董其昌笔法成就平平,但对章法却别有会心。他的作品结字随遇而安,自然优雅,远胜于赵孟頫、文徵明那种程式化的处理,字字意态联属,生动可人;作品行间距离较宽,与疏宕、洒落的风韵相辅相,成一这虽然源之于《韭花帖》,但却是由董其昌将它发展为表达审美理想的重要手段。
对赵、董人进行全面的评价,非本文所能及,我们不过将他们作品的主要特点进行比较,以见出笔法与章法相对地位的转移。他们二人对元、明书坛具有足够的代表性。至于清代,例子便不胜枚举了。
书法艺术形式因素之间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主次高下,既有作品之间的区别,又有作者之间的区别,更有观赏者审美习惯的区别;如果不把这种观系放在历史的运动中来考察,恐怕永远也理不出头绪。
对任何一种艺术来说,各种形式因素都有自己创始、发展、成熟的过程,这些过程不尽相同,因此便形成特定时期特定形式因素的繁荣。如“永明体”,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地位并不高,但它对汉语音律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活跃于十九世纪欧洲画坛的印象派,在构图上并不曾表现出足够的创造性,但是在色彩的运用和外光的表现上,却开闢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书法史上笔法、章法、墨法的最高成就,也不是在同一时期取得的。当我们对它们各自的发展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并且进行认真的比较研究时,便有可能找到各种形式因素轮替消长的历史规律。
限于题旨,以上讨论都是从形式自身的发展来看问题。审美理想对形式发展的制约作用是问题的另一方面。
特定的艺术风格总产生于形式发展与审美理想发展的交点之上。例如我们说到怀素的选择。他之所以具有这两种可能,是因为他处在两种笔法的交替时期,形式的发展为他准备了向前、向后两条不同的道路;他之所以选择前者,是因为唐代慷概、壮阔而升沉变幻的生活陶冶了数代人的,也包括他的灵魂。
离开形式发展的历史,离开审美理想的变迁,无法对各种形式因素的消长规律作出准确的叙述。关于笔法、章法孰主孰次的问题,若干世纪以来争论不休,便是出于这样的原因。
现代书法从笔法的空间运动形式来说,不曾增添新的内容,而线条结构的变化却层出不穷;其次,现代艺术要求风格强烈,促使作者更多地考虑作品给予观众的第一印象,这使章法处于更为突出的地位;其三,墨法由近代以来的迅速发展,使它在现代书法中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手段,它分散了人们对笔法的一部分注意力。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成为忽视笔法的理由。笔法控制线条感情色彩的作用,始终是不曾改变的。一件作品除了宏观效果外,是否具有持续感人的力量,首先取决于笔法的得失。
对现象的考察已经告一段落。现象之下,似乎还隐藏着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
笔法发展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主要原因是否发生过变化?……
笔法发展的推动力来自两个方面:实用的要求与审美的要求。自从人们意识到书法的审美价值以来,这两种要求便始终同时存在。前者要求简单、便捷,后者却要求变化丰富。这种矛盾伴随着整个书法史的进程,只是不同时期处于主导地位的要求不同。
由于讨论涉及字体变迁,我们可以根据字体的进化把书法史分为两个时期:楷书确立以前为字体变化期,楷书确立以后为字体稳定期。从时间上来说,前后两期约略相等,各占一千馀年。但是,字体变化期中,字体的变化集中在后一阶段,即战国至东晋,这一时期,大约每隔三、四百年字体便发生一次重大的改变;字体稳定期与此恰成鲜明对照,楷书确立后的十几个世纪中,字体不曾发生任何变化。
仅仅这一事实,便提醒我们,前后两个时期可能存在某种极为重要的区别。
字体的变化包括两个方面:结构的变化与笔法的变化。字体变化期中,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结构不断趋于简化。这无疑是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对作为交流工具的文字施加影响的结果。笔法的变化与结构的变化虽然始终互为依存,此时结构的简化毕竟是事态的主要方面。实用的要求左右了字体结构的发展,而字体结构的发展又成为从形式内部推动笔法发展的重要原因。这一时期笔法的发展从属于字体的变迁,审美的要求服从于实用的要求。但是,书汉字字体发展趋于稳定之后,也就是说楷书的地位确立之后,字体结构不再发展,从形式内部推动笔法发展的原因消失,笔法最本质的一个方面——空间运动形式,由于缺少变化的内因,再也无法向前发展,增添新的内容。字体变化期中,笔法从摆动发展到绞转,并完成了绞转向提按的转移;字体稳定期中,笔法便“稳定”在提按范围之内。
从实用的角度来说,绞转变为提按,由点画自始至终的变化变为端部与折点的变化,是一种简化,是一种进步,但是从审美的要求来说,却是非常不利的一面。不过,这迫使笔法从空间运动形式之外去寻求发展,迫使书法艺术从笔法之外去寻求发展,这对丰富书法艺术表现形式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然而更有意味的是,由实用要求促成的字体变化停止后,尽管社会的发展仍然不断对文字提出简化的要求,但得不到丝毫的反响。失去反响的要求,必将失去它存在的意义。于是,对于笔法的发展,实用的要求不得不让位于审美的要求。因此楷书确立后,笔法的发展有了崭新的含义:它不再受制于实用的要求,而主要是一定时代审美理想的产物。
这种审美要求的解放,不仅对笔法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对整个书法史的发展,它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审美的书法与实用的书法从此分道扬镳,拉开了距离。唐代以前的书法作品,大部分是简牍、碑铭等应用文字,它们的艺术性只是这些文词的附庸,后人之所以把它们主要当作艺术品来欣赏,不过是己经习惯于把文词与书法倒过来看而已,就像我们早已习惯把视网膜上的倒像认作正像一样。唐代才开始较多出现有意识作为艺术品而创作的书法;他们是在哪一天决定要这样干的呢?唐代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当然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形式内部,不可能不蕴藏着深刻的契机。
书法很早便成为一门自觉的艺术,但审美要求的真正解放,始于楷书的形成。
这是我们从笔法发展原因的讨论中产生的最初的思想。但是接着便出现了两点疑问:其一,隶书与楷书的形成同是字体简化的环节,为什麽前者促使笔法丰富而后者促使笔法简化?其二,字体发展到楷书后为什麽不再发展?还能不能发展?
如上所述,字体变化期中,结构的简化是第一位的要求。审美的要求可能使隶书增加了一些挑拂,使楷书保留了捺脚等等,但从结构的整体来说,简化是明确无误的标记。随之而来的笔法运动形式的变化,完全受实用要求的制约,受结构简化的制约,人们仅仅选择适合新的字体结构的笔法,加以充分发展:隶书和草书选择了绞转,楷书选择了提按;至于哪一种运动形式使笔法丰富,哪一种运动形式使笔法简化,并不与结构的简化成正比,而由各自的运动性质所决定。这些,前面论之已详,毋庸赘述。
我们知道,字体变,笔法空间运动形式也变;字体变化停止,笔法空间运动形式的变化亦停止。一定的字体结构总是与一定的笔法联繫在一起的,例如隶书与绞转、楷书与提按,便是一对对应运而生的孪生子。既不可能字体结构改变而笔法不变,也不可能笔法空间运动形式改变而字体结构不变;字体结构与笔法的空间运动形式便处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中。
由此可知,字体停止发展,同笔法空间运动形式停止发展密切相关。如果我们找到笔法空间运动形式能否继续发展的证明,对字体能否继续发展便可以作出相应的判断。这一设想促使我们思考笔法可能具有的各种空间运动形式。已有的:平动、绞转、提按,将有的呢?这是书法史无法解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