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宋四家”之首,苏轼不但以其极具个性的书风独步当时,同时也以其独特的书法美学思想对当时及后来的书坛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探究苏轼的书法美学思想是困难的,因为苏轼在谈到自己的书法美学思想时,大都语言简短、浓缩概括,缺乏现在人所谓的系统和周密。下面,我们尝试依据中国传统艺术观的独特语境,对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作一大致描述。
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最为人们所熟知的是他尚“意”的观点:“吾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苏轼书法美学思想中尚“意”的观点,代表着整个有宋一代的书法美学观念。清代书论家梁巘,说:“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元明尚态。”也就是说,与晋代追求的韵味、唐代追求的法度、元明追求的形态不同,以苏轼为代表的宋代书法艺术家所追求与表现的是“意”。
看来,理解苏轼书法美学思想的关键正在于他所谈到的“意”。
“意”在中国传统艺术美学中是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语词,远不如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样简单。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意”,已经钝化、磨平为一个非常普通的语词。在中国古代艺术,尤其是书画艺术所要传达的“意”,往往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连在一起。李佐贤《书画鉴影》中,记载有明代书法家祝允明有关艺术之“意”的一段妙论:“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得其意而点出之,则万物之理,挽于尺素间矣,不甚难哉!或曰:‘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不知天地间物物有一种生意,造化之妙,勃如荡如,不可形容也。”祝允明这段话虽然主要是针对画之“意”来说的,但由于中国传统书画一体同源,因而此处之“意”,对于书法艺术同样有效。在这里,祝允明赋予了绘画之意以非同寻常的内涵:“意”首先与“形”相区别,绘事不难于写形而难于得“意”,但“意”不仅是与形相对的“神,’;其次,“意”也不仅是画家的情绪意念。祝允明显然反对那种将画意内涵仅仅规定为画家主观意绪的观点,批驳了“草木无情,岂有意耶”一类话难。在祝允明看来,画之意首先是一种显现“万物之理”的“生意”。他劝导把画意局限于物之神趣或自我之情意的人们放远眼光,大其心胸,纵览天地万物,在感受宇宙造化之妙的同时,领悟天地万物间的生生之意,从而将这一浩然之意点写而出。

与“艺道合一”艺术美学观念相应,书艺尚自然在苏轼书法美学观念中也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就书法所营构的“象”来讲,书法的点画、字形和整体布局,都应该呈现自然之态。书法艺术营构之象往往是宇宙自然万象的高度提纯,其灵动的点画皆指向大千世界生动丰富之致。因此其自然之趣就主要体现为书法形象,包括点画结体以及篇章的生意生趣。本来,一切艺事都是“以万物为我”,都是使用符号(意向)以表现自我对“道”的体认。苏轼于此体验甚深。他在《跋君漠飞白》中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在《次韵子由论书》中亦说:“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通其意,既指篆、隶、行、草之必然的规律联系,更指书法与大千世界万事万物之必然的规律联系。他在《净因院画记》中提出艺术表现的“常形”“常理”说,指出艺术表达自然之“常形”、“常理”,“千变万化,未始相袭,而各当其处。合于天造,厌于人意。盖达士之所寓也软。”“合于天造”,即客观事物得到直接、间接的再现;“厌于人意”,即主观意趣(其中含融对道的体认)得到完善的表达。他在《授经台》诗中说的“剑舞有神通草圣,海山无事化琴工”,就是这一观念的生动表现。其二是就书法创作过程中的运作特点来讲,书法创作应自然而然。他在《小篆般若心经赞》中说:“心忘其手手忘笔,笔自落纸非我使。”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说:“手必至于忘笔而后能书……及其相忘之至也,则形容心术,酬酢万物之变,忽然而不自知也。”《题鲁公书草》中说颜鲁公的草书奇特,是因为“信手自然,动有姿态,乃知瓦注贤于黄金。”总之,强调要不经意,出以自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与大道的运化过程以及创生之物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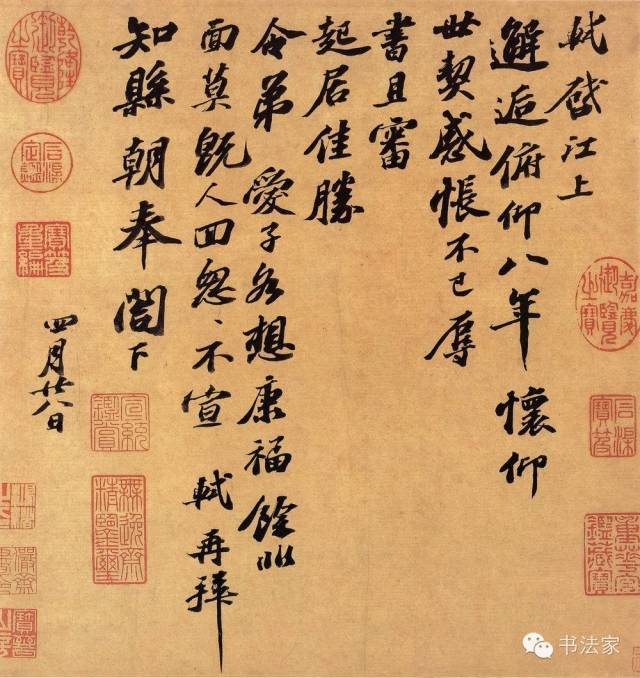
因此,书在发生之初就不是源于一种模仿外物的冲动,而是出于“穷天地之变”的宏愿,这使书艺一开始就摆脱了具体物象的拘泥,而在所营构的形象上是取高度提纯的点画,以此象征自然界“勃如荡如”的生生之意。显然,书法作品中的点点画画既然源于自然万物千形百态的高度提纯,它们就完全具备让观赏者将它想象、还原为自然万象的客观机制,就可以让人们在欣赏它们时体会到自然万物的勃勃生机及其内在生命力。
笔画的力度、形势的表现,不外是以其所含的巨大潜能,吁请着自然万象及其能量,也正因为如此,书家们都规定了运笔的法则:“将欲顺之,必故逆之;将欲落之,必故起之;将欲转之,必故折之;将欲掣之,必故顿之;将欲伸之,必故屈之;将欲拔之,必故之;将欲来之,必故拓之;将欲行之,必故停之……”。在“逆”、“起”、“折”、“顿”、“屈”、“”、“拓”、“停”时,笔画因受阻而具有了巨大的内蕴和潜在的爆发力。只有笔画达到如印印泥,如锥画沙,如屋漏痕,如折钗股的效果,方能充分显现洋溢于宇宙天地的自然之力。
笔画是这样,字的结构也是这样。灵动的笔画须通过一定方式的组合构成一个个生气贯注的字,是为结体。从历代书家有关结体的论述来看,同样强调对“生意”的表现。张怀瓘就说:“其一点一画,意态纵横,堰亚中间,绰有余裕,结字俊秀,类于生动,幽若深远,焕若神明,以不测为量者,书之妙也。”也就是说,书家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应成为生气贯注的有机体。因此,结字时,一点一画,左右上下首先应布置停匀,又能回抱照应,而不可头轻尾重,左短右长,伤密伤疏。好的结字,每个字皆应“上称下载,东映西带,气宇融和,精神洒落”。如果说书艺笔画的要求还有一定的恒定性,那么,结字则因书家个性、气质与时代环境的差异而表现出不同的风貌,表达着书家对自然“生意”的领悟。
为使书艺从根本上成为自然之意的表达,一个个生气贯注的字体还必须由精心的布局而形成生意盎然的整体。章法与布局,说到底仍是追求全幅作品流溢的生意生气,所谓:“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仅能写好单个的字,从来算不得个中高手,书家的工夫,在于能从整体上对每个字作适当的处理,使之服从于“生意”整体的表现。所以,书家历来推崇发于无意的“一笔书”,米芾就说“欧、虞、褚、颜、柳,皆一笔书也,安排费工,岂能垂世”。“一笔书”的实质,就是强调全幅作品生意的贯注,使整个作品真正成为大道运化之迹。所以,古人有云:“深识书者,唯观神采,不见字形,若精意玄鉴,则物无遗照,何有不通。”对于书法营构的象,苏轼这样说:“书必有神、气、骨、肉、血,五者阙一,不为成书也。”显然,在苏轼眼里,书法作品中的文字及形体排列,已作为一种艺术形象而成为了活的生命有机体,“神”、“气”、“骨”、“肉”、“血”五者皆备。因此对书之象,无论是点画、结字,还是布局,都重在强调生气生意的贯注,如是观之,书法创作为一种活的生命的创造。
就“神”、“气”、“骨”、“肉”、“血”五者而言,“神”在书论中往往指书象内在的精神与灵魂,如“凡书,精神为上,结密次之,位置又次之”。“气”则是指流溢于书象中的生动之气,如“作书贵一气贯注”。在古代中国人的哲学观念中,“气外无神,神外无气”,“神”“气”往往一体,故而在书论中我们常常看到“神”“气”合称并举:“不由灵台,必乏神气。”“学书之要,唯取神气为佳,若模象体势,虽形似而无精神,乃不知书者所为耳。”“神”“气”作为书象内在的生命机质,显然是至为重要的,它们决定着整个作品的精神气质,是一幅书法作品成败的关键,书象只有“神”“气”充盈,才能真正显示其生动活泼的自然生命。
相对于“神”、“气”、“骨”、“肉”、“血”是书象的外在生命形态。“骨”指构成书象的、具有坚定刚健力道的点画,所谓“(手)指能实则骨体坚定而不弱”;“肉”与“血”则是指点画中的墨与水,所以说“血生于水,肉生于墨,水须新汲,墨须新磨,则燥湿调匀而肥瘦得所。”
于是,“神”、“气”、“骨”、“肉”、“血”五者,分别从内外两个方面决定了书象生动活泼的自然生命。“神”、“气”尽管是内在的、无形而难以捉摸的,但它们却可以借形于外的“骨”、“肉”、“血”而得到显现,“骨”、“肉”、“血”尽管已“物质化”为抽象的点画,但其蕴涵的“神”与“气”又无不显示着它们都是生命运化的轨迹,是形质动荡、神采飞扬的活的生命。苏轼以此番描述生命体的话语言说书象,其看重书艺生命意味的倾向十分明显。
既然把书象作为生命形象来塑造,因此像诗画的创作一样,苏轼特别强调书法创作过程中发于无意的“自动化”运作。
在历代书家看来,书法创作过程中“自动化”的运作,最能体现这门艺术对自然的追求:“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扶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及其悟也,心动而手均,圆者中规,方者中矩,粗而能锐,细而能壮,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思与神会,同乎自然,不知所以然而然矣。”发于无意的“自动化”运作,此处的“无意”,并非原始、自发之意,这里的“无意”实际是对原始自发的否定之否定,是对习书过程中“有意”的超越。在这一阶段,创作主体因能迅速地进入运作过程自身的“逻辑”,因而他仿佛已不再处于主动的地位,而是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主宰、所引导。创作达到这种如厄丁解牛般的境界,就是“化境”,就类于大道创物。对于这种达于自然的创作境界,苏轼无论在文学、绘画,还是在书法领域,都一贯地推崇这种自然而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的境界:“仆以为知书不在笔牢,浩然听笔之所之,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一方面是“浩然听笔之所之”,一方面是“不失法度”,这是书法创作过程中对运作过程自身“逻辑”体认与进入的必然结果。这种创作境界,一般意义上的“法度”、“规则”,已经不再是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法规,而是转化为一种内在的律令,向无意识领域积淀。表面看这种创作没有了规矩,实际上却无一不中规合矩。在书法创作中,苏轼最忌的是为“法”所役,为“法”所困:“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限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
为“法”所困,表明“法”还是一种外在的约束,一种未被认识和掌握的规矩,在这种情况下,创作者是无从体验到快乐的,因为他处处受约束,处处不自由。这往往是艺术家习艺阶段常见的现象,经过较长时间的训练,当“法”一旦被认识、被掌握,创作者就能体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但就是这样,也还不是创作的最上乘境界。在苏轼看来,创作达于这一层面,至多是掌握了前人所创立的法则,仅获得了一种有限的自由,创作要达到最高的自由,必须从掌握前人的法则发展到超越前人的法则,“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正充分表明了苏轼对这一创作境界的追求。因为这一境界,意味着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融入了自己对艺术规律的理解,艺与“道”的统一真正通过艺术家自我这一中介而实现,这时的艺术家,往往能通过随心所欲的创造体验到“造物者”的自由。表面上看,此时的艺术家不遵循任何法则,但他实际所理解与掌握的是“乾坤旋转之义”,遵循的是天地之大法一大道之运化,所以,石涛后来说,“无法之法乃为至法”。对这种“无法之法”,苏轼借评王安石书法这样说:“荆公书得无法之法,然不可学,学之则无法。”
也就是说,“无法之法”意味着对前人陈法的完全消化,当创作者完全突破前人的樊篱,他所遵循的“法”就不再局于某派某家,而是在领悟大道、与道一体的基础上效法大道自然而然的运作。这一层面的“法”,当然是不可学的。其实,可学的“法”,皆属于形而下者、浅而小者。它们都是技艺层面的。
苏轼对“无法之法”的倡导,是他尚“自然”的艺术美学观念在创作领域的典型体现。在现实中饱受压抑的主体生命,必须在艺术的领地中得到自由的宣泄,所谓“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正是抱着这一坚定的信念,苏轼对前人创立的法则与其说是继承与掌握,毋宁说是打破或超越。因为,各种各样的法则、规矩制约着主体生命的释放,主体生命必须冲决一切陈规陈法的束缚,以前无古人的气概,方能凸显生命本身自然运动的特征。由于苏轼在根本上认同于大道创化的宇宙观,追求生命的自然状态,因此苏轼对生命自然自由状态的看重,并不就导致其因对自我的片面夸大而走向绝对的自我表现,甚至走向“为自然立法”,凌驾于自然之上。苏轼所追求的是自我生命与宇宙大生命的融通合一。
苏轼的这些追求,比起前代书家来,有什么不同呢?是因为他对于书艺修习的三个阶段、或者说三种运动形态、三层次规律有明确而深刻的把握。首先,初学必有一个舍我从法的阶段,《题二王书》说:“笔成家,墨成池,不及羲之即献之。笔秃千管,墨磨万铤,不作张芝作索靖。”在《跋陈隐居书》又说:“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尝庄语而辄放言,无是道也。”这就是要跟着客观法度走,熟谙第一层次的规律。第二阶段是入“法”后,就要从法中出,即由艺进道,呈现自我独特之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二首》(其一)说:“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神。”讲的是这个主张。《书吴道子画后》说:“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更是明确地强调此意。这也就是我们在前文说过的“吾书意造本无法”的阶段。在《评草书》中讲:“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自我意识的高张,可谓欣然自得。但是,舍我从法之时,难免有执于法而障性灵之病;舍于法而张扬己之时,又难免有执己之偏。于是,必然还得追求一个更高的境界,就是进到无法而有法,无己而有己,即法即己,即己即法的阶段,也就是上文刚才分析过的“无法之法”的阶段。法与意的化合,似乎法即意而意即法。《评草书》中说:“书初无意於佳,乃佳尔。”《戏咏子舟画两竹鸜鹆》中说:“千变万化皆天机。”描绘的都是这种无彼无我而即己即我的融通境界。
因此,将苏轼书法美学观念中所尚之“意”理解为创作主体的情绪意念,根本上说就是一种不小的误解,这种误解很轻率地将苏轼乃至整个有宋一代尚意的书法美学观念仅仅理解为抒情主义或主观主义。其实,中国艺术美学思潮中很难找到纯粹的抒情主义或主观主义,即使有这种倾向的言论,那也是建立在天人合一、艺道一体的哲学美学观念上,“自我”这一在西方美学中倍受崇拜的概念,在中国哲学与美学中却常常被置于形而上的“道”之下,自我往往不是走向自身,而是走向宇宙大生命—“道”。有时,为了消解日常状态中太强的主体意识,苏轼有时还借助于酒精的力量。
苏轼爱酒、饮酒甚至亲自酿酒,但他又绝不是一般痴迷于酒的酒徒,为此,他还嘲笑过嗜酒贪杯的陶潜和刘伶。苏轼饮酒只求酒中的乐趣,不求一醉方体。他酒量本来不高,对酒的反应极端敏感,酒性往往来得猛、来得快,常常是一杯酒下肚,即醉眼朦胧。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苏轼的灵感往往纷至沓来、势如泉涌,酒这个时候就成了“钓诗钩”。像他笔下的许多文学名作,诸如《大江东去》、《赤壁赋》、《明月几时有》以及大量的书画作品,都是酒后所作。他在一首诗中专门谈到了酒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空肠得酒芒角出,肺肝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涴壁常遭骂。不慎不骂喜有余,世间谁复如君者。一双铜剑秋水光,两首新诗争剑芒。剑在床头诗在手,不知谁作蛟龙吼。”
尽管此诗是针对绘画而言,但它所指涉的情形,同样适合于书法创作时的情况。苏轼就不止一次地谈到酒在书法创作过程中的作用:“吾醉后能作大草,醒后自以为不及。然醉中亦能作小楷,此乃为奇耳。”醉与未醉时的创作状态是全然不一样的。草书,比其他任何书体更加强调一气贯注,气脉不断,因而更为趋近于那笔随心运、发于无意的“自动化”运作,因此也就更为逼近于大道造物的自然而然。它并不重在一笔一画的精心营构,而是更为重视灵感状态中的放任挥洒。要达到这种境界,就尤其要求创作者对日常心理状态的超越。为此,刘熙载说:“欲作草书,必先释志遗形,以至于超鸿蒙、混希夷,然后下笔,所谓“释志遗形”,那显然是日常状态中无法办到的,借助于酒的力量,创作主体才能脱离常态,产生对宇宙大化、生命自然的深刻领悟,从而爆发灵感,一挥而就。苏轼的确有酒在自己创作过程中充满神奇力量的真实体会:“仆醉后,乘兴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这一经验之谈,不外强调酒能强化创作主体的生命体验,使原本与创作者有间的生命元气与创作者透明无隔。艺道合一的艺术美学观,使书法创作的上乘境界,仍然应该是“默契造化,与道同机”的自动化运作。
这样,书法在苏轼的眼中,就成为最接近自然、也最自然的艺术。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根据苏轼以上的观点,以之与下面书法理论史上的言论相互参照来加以理解:“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则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观夫悬针垂露之异,奔雷坠石之奇,鸿飞兽骇之姿,鸾舞蛇惊之态,绝岸颓峰之势,临危据槁之形,或重若崩云,或轻如蝉翼;导之则泉注,顿之则山安;纤纤乎似初月之出天崖,落落乎犹众星之列河汉;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
综上所述,在中国传统艺道合一的艺术美学观的深刻影响下,苏轼坎坷的人生历程促使他必然以“自然”作为其书法艺术的基本美学观念。在苏轼那里,“自然”既是指书法形象的自然之态,也指主体艺术创作过程中仿佛发于天然的“自动化”运作特征。苏轼书法观念上尚“意”的实质,即是崇尚“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