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我只讨论传统风格的书法创作。
人们经常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作品才是一件出色的传统风格书法作品?我认为,一件真正优秀的传统风格书法作品,它既能唤醒我们对传统中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的回忆,又能使我们感觉到一些从来不曾感觉过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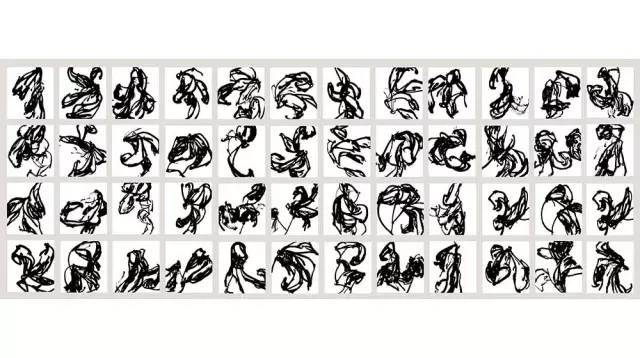
由于强调创作中人的表现,个人风格的形成是缓慢的,形成后不容易变动,同时一个人通常只能创作出在不大的风格范围内变化的作品。这是书法史上数千年以来的基本状况。
现代社会状况的改变,影响到书法的生存状态。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点:一、毛笔不再是日常书写的工具,它破坏了人们通过日常书写而使“人”与书写融合的机制;二、书写人口的扩大及其知识结构的改变,使会写字的人、爱好书法的人不一定具备传统文化修养,这使得人们对书法的感受难以不断深入;三、艺术观念的变化,使人们总是以现代意义上的“艺术”来要求书法,现代文化中艺术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它与传统文化中书法的地位有质的区别。
这些,对当代文化中书法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各级院校书法专业的设置,强化了这种趋势。现代书法专业教育,培养的是书法艺术家和书法工作者。这是一种社会分工,受教育者必须负担起为整个社会服务的责任。专业教育培养的绝不仅仅是具备传统书法修养的人,现代书法艺术家和书法工作者必须在专业有关的一切方面作好准备。这种专业教育中有发展个人精神生活的内容,但占用更多课时的,是从专业设置出发而规划的全面的知识、技术和感觉上的训练。
当代文化的有关状况,使现代书法创作注入或强化了过去没有,或不大被重视的因素,例如想象力、趣味等。
这种变化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是书法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与整个艺术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有利于社会的吸取与享用,也有利于向当代艺术的渗透;不利的一面,是对形式的高度关注,会使人忽视书法后面还有一个“人”的存在。
作为修养的书法和作为艺术的书法在今天必须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一件作品,只要它还让我们想起“书法”,我们便无法抹去对所有有关传统的记忆。此外,忽视作品后面的“人”,会使我们无法真正深入传统杰作的核心。
对“人”的强调不是一个新的话题,但今天我们重新强调这一点,却有一层新的用意。
最近20年人们对传统技巧把握的进步,使我们可以对书法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如何把传统风格书法继续做下去,有两条思路。其一,如人们经常问到的:未来的书法是什么样子?——仅仅着眼于具体的形态,这是不会有答案的。艺术的魅力之一,便在于它的不可预计,任何预计都与想象力的性质相悖。另一条思路,便是去寻找艺术不断深入的道路。
“人”的深入,是当代书法创作深入的一个重要途径。在技术问题普遍不曾解决的时候,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会使作品有明显的变化,但技术达到一定水准以后,作品的精神状态,或者说意境,成为至关重要的方面。
人们所未感觉到的东西,对于他来说不存在;处于人们感觉水平之上的东西,他只能把它拉到自己的感觉水平上来认识。因此,在我们自己的感觉之外,必然存在一个更高水平的作品的世界。只有“人”的状态达到一定水平时,这个人才可能感受到隐藏在杰作中的相应的那一层精神与形式的关系,才可能借此而获得一种更高水平的鉴赏力和判断力。——它们是创作更优秀作品的前提。
人们在突破已有的感觉水平的界限时,无法仅仅从自己专业的形式与技巧中获得支持。一位伟大的作家曾经说过:“小说家不能仅仅从别人的小说中获得灵感。”要突破前人在书法创作中已经取得的成就,只能从它处寻求支持。
提高“人”的水准——深入杰作——转而以所领悟的关于创作的更高水准为基础,发展出新的关于创作的理想;然后再在所有能想象的方面寻求技术与构成上的支持。这或许是让传统风格创作不断深入的道路。
在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于右任、林散之、陆维钊这样杰出的书法家,使我们对书法创作的前景充满信心。狭义的书法史——传统风格书法的历史,必将继续书写下去。我们时代已经创作出无愧于前人的佳作,也必然继续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无法回避的是,狭义的书法史在今天已退居边缘的地位。书法虽然拥有众多的爱好者,但它对相邻学科、对当代文化都缺少影响力,就是像林散之这样出色的书法家,也不曾对中国绘画,更不用说对当代文化产生重要的影响。其实,这部狭义的书法史与那部广义的书法史——包括传统风格书法、现代风格书法和源自书法的艺术作品在内的总体书法史,与中国当代艺术史、文化史,始终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书法,不论是在学术上还是在创作上,都应当在当代文化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关于这一点,最近几年,已经开始表现出种种迹象。
